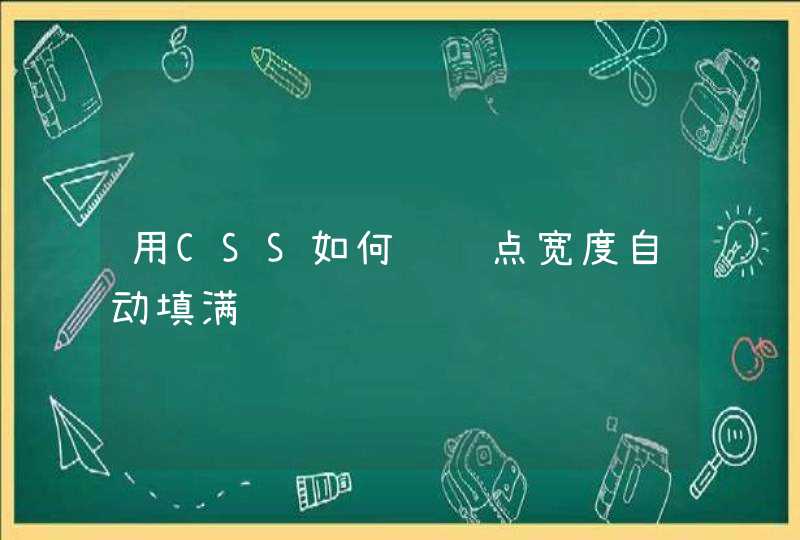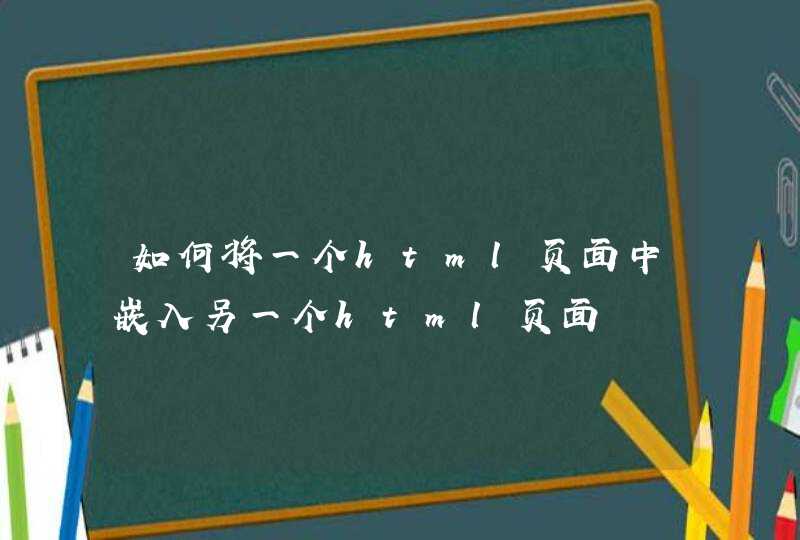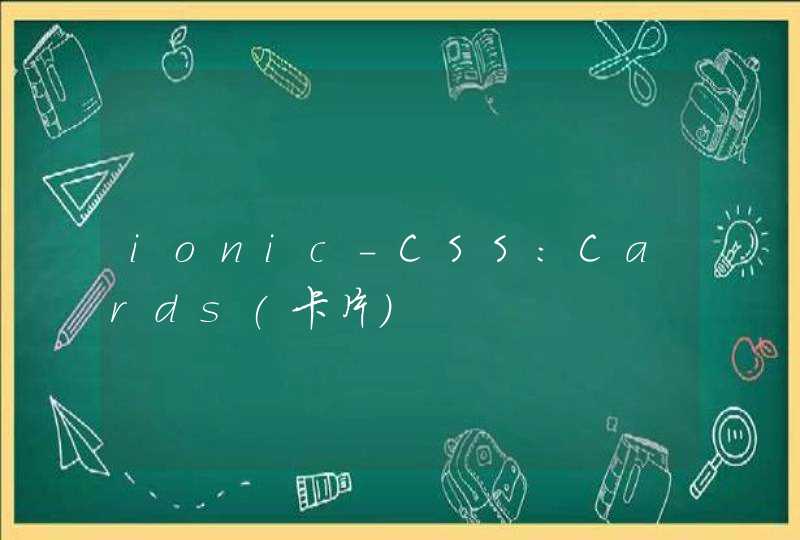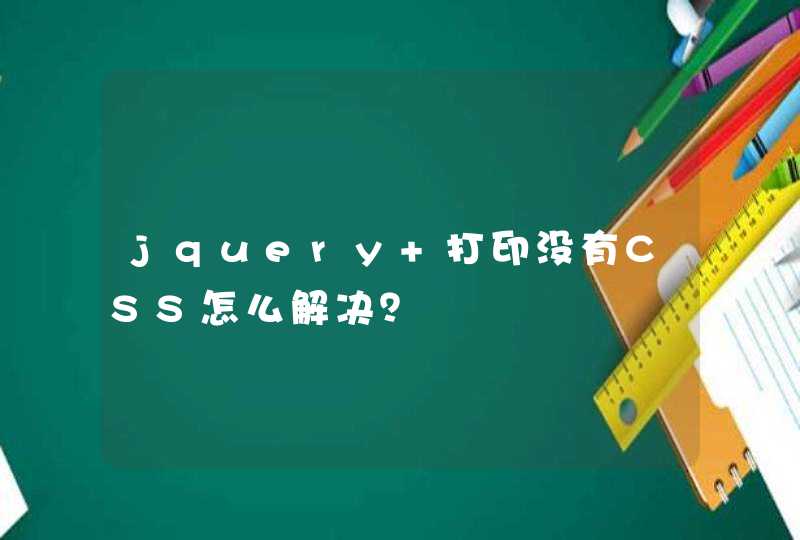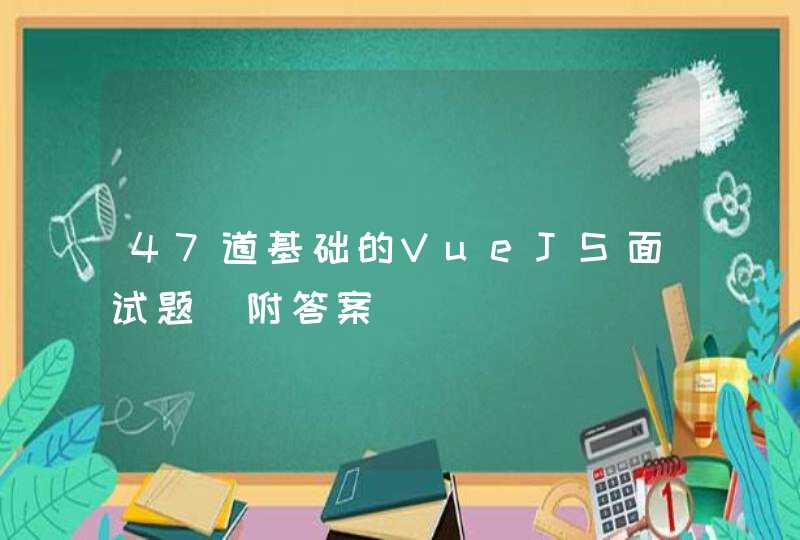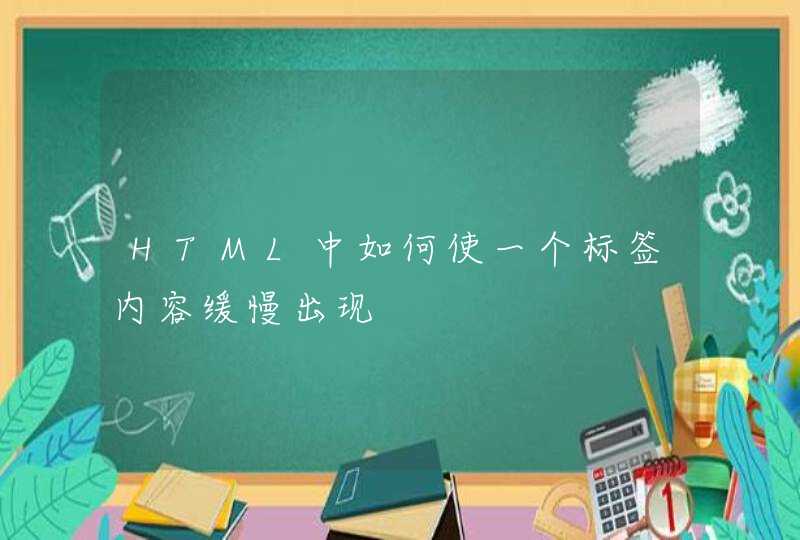
母亲是退休的小学教师,她在这教了二十多年书,这有她好多的学生,付食品店的女售货员、街头拐角处那个修表的……当然还有好多后来上了大学的。母亲上街的时候总有人给她打招呼,除了她的学生叫她余老师外,其他的人都叫她余太婆,叫老师也好,叫太婆也好都表示了对母亲的一种尊敬。我在新疆工作,回家的机会不多,每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,陪母亲上街时,遇到有人不停地向她问好,她都满面春风地回应人家,母亲生活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,是很愉快的,在我的面前甚至还有几分的自豪。
母亲是江苏常州人,出生在大户人家,母亲的父亲余少舫早年曾当过宋子文的秘书,曾任常州知府、杭州府烟酒局局长等职。母亲的伯父余大鸿曾是清军协统,1912年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。其子余纪忠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要职,后成为台湾报业巨子。母亲的兄弟姐妹很多,都受过良好的教育,母亲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英专系,此间认识了同学褚璆后结为伉俪,后因时局动荡,父亲去世,家道中落,携小妹随丈夫辗转于当时的大后方川、滇、黔一带,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上海,这时母亲已有三个孩子了,寄居在我们父亲的哥哥家中。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们的大伯是一个忠厚纯朴的工人,很小的时候就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,解放前夕参加了中共地下党,后来是这个厂的劳资科长。
原以为抗战胜利了,能过上安生的日子,谁知时局还是那样动荡,为了生计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跟随父亲,四处漂泊,先后到过杭州、南京、株州,长沙、醴陵、衡阳好多地方,一九五二年到武昌后,才算安定下来。受孩子的拖累母亲没有办法到社会上去工作,那时,我和哥哥都在武昌铁路第一职工子弟学校上学,四弟和五弟也大了一点,母亲总想找机会出去工作,正好铁路局办的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缺老师,虽然不是正式的,待遇也很微薄,母亲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,来往于武昌和汉口之间。来学习的都是成年人,他们的文化底子都很薄,程度又参差不齐,母亲的脾气特别好,为人又忠厚善良,对每一个学员都认真负责,时间一长,学员们都很喜欢她,有些跑车的列车员出差回来时还想着老师,总给母亲带点外地的土特产。
母亲终日操劳家务,学业几乎荒废。记得到武昌后不久,武汉市教育局面对社会招聘教师,考试中母亲还闹了个笑话,有一道题是翻译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中“刻舟求剑”一段文言文,母亲竟然译成找到了楚人掉到水里的那把剑。考试回来,母亲问我,到底能不能找到剑,连我这个上四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,母亲懊悔不已,开始了新的学习过程。母亲的小妹妹是读师范的,和母亲一起参加考试,成了武汉市球场路小学的正式教师。
生活上的许多事母亲也在不断地学习,那时候都烧煤球,生炉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,弄不好烟子薰得你直流眼泪,炉子还是生不着,慢慢地母亲找到了窍门,柴禾要架空,堆上煤球后要慢慢地捂着,快了柴禾烧完了,煤还着不了,心急是没有用的。用体温表测体温,母亲不知道怎么看,先放在刚从热水瓶倒出来的开水上试一试,热气一薰体温表涨破了,水银流到地下到处乱滚。母亲是南方人,很少吃面食,更不要说做馒头了,酵头也放了,可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酸,母亲竟然不知道发好的面里要加碱或是小苏打,看着那冷了以后还发红的馒头,母亲自嘲说这是“洋”馒头。装卸供应社工会主席的爱人姓崔是河南人,会做面食,母亲请她到家里来手把手地教,直到蒸出又白又松软的大馒头来,母亲高兴得笑了。母亲不太会做针线活,看到有的妇女把新袜子剪开上袜底,这样的袜子结实耐穿,想剪又不敢下手,最后还是没学会,我们穿袜子又特费,只好破一个洞补一个疤又厚又难看。更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学会了做棉布鞋,一针一针的纳鞋底,做出的鞋虽然不是多好看,但穿在脚上却很暖和。“三反、五反”的时候,父亲受冤被关押,停发了工资,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,我和哥哥也失学在家,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给隔壁的油条铺捏煤球,好心的店主故意多给我们一点钱;母亲煮了好多的五香茶鸡蛋,让哥哥和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去卖;母亲事带着我们到郊区的菜农那,拣包包菜的叶子腌成咸菜;母亲还挎着竹篮装上香烟火柴、人参米、针头线脑等小东西到余家头去卖……母亲从一个大家闺秀的小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我也记不清楚了,什么时候民间办学又再度兴起,母亲成了民办学校的教师,民办学校条件差,教师待遇又低,母亲毫不计较,母亲觉得能走上课堂就是庆幸的事了,认认真真地备课,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,一心一意地为着学生。母亲的毛笔字、钢笔字、粉笔字都写得很好,母亲会弹风琴,能自弹自唱,歌也唱得不错,主动兼教音乐课,那时即使在公办学校能用风琴教音乐课的人也不太多,母亲的音乐课为她所在的民办小学增色不少。这时我们家也从武昌搬到了汉口。也记不得是那一年了,总之是过了好多年头,母亲所在的民办小学终于转成了公办学校,母亲和她的妹妹一样成了公办教师。母亲从内心深处感谢新社会,感谢党,工作学习的热情更高了。
母亲以她的善良,她的厚道来对待她的学生,她的同事,她的邻居,她周围所有的人。一次母亲在一个班上音乐课,刚下课,一个调皮的男学生在课桌间奔跑,一不小心摔倒了,额头撞在桌子角上流出血来,母亲立即把学生送到了学校旁的诊所,自己出钱,治疗包扎后把学生送回了家,一开始家长还以为母亲有一定的责任,脸拉得老长,母亲觉察到家长的不快,没说什么就走了,第二天母亲又去看望这个学生,家长已从孩子的叙述中得知事情的原委,很不好意思地连连向母亲道歉,感谢母亲对孩子的关怀。母亲当了教导主任,对老师都一视同仁,听课后都充分肯定老师的长处,发现问题时也能与老师真诚地交流,母亲的真诚是出自内心深处的,也是感人的。有一个老师在文革中贴过母亲一张大字报,说余主任是县太爷的女儿,这也是文革中贴母亲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,母亲一直都不知道这张大字报是谁贴的,时间长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,谁知,贴这张大字报的人自己却耿耿于怀内疚得很,因为平时母亲很关心她,教学上母亲给予她很大的帮助,在评先进时充分肯定她的成绩,她的孩子生病时,母亲主动替她上课,她实在是憋不住了,找到母亲说自己对不起人,母亲很平静,告诉她事情都过去了,不要放在心上,后来母亲一直对她很好,母亲退休后,这个老师还经常来看望母亲。有一次母亲上街的时候,被一辆偏三轮摩托车挂倒,开车的是两个解放军,他们俩一看摔倒的一个拄手杖的老人,吓得不得了,连忙把母亲扶到路边的一个小店里坐下,母亲感觉头有点晕心有点慌,看到站在面前的两个手足无措的年青人,母亲只是请他们赶快找点水来,喝点水定定神,两人急急忙忙找来一瓶矿泉水,喝完水母亲好了些反过来安慰两个解放军说:“你们别着急,再过一会我就好了。”其中一个发现母亲的脸上有点擦伤,要送母亲到医院去检查一下,母亲觉得没什么大碍不想去医院,两个解放军又说送母亲回家,母亲不想为这点小事惊动左邻右舍,也婉言谢绝了。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,两个解放军很不好意思地走了。身为医生的大哥知道这事以后,立即给母亲作了检查,还好只是脸上和小腿有轻微的挫伤,大哥嗔怪母亲没有记下摩托车的车号,没有让两个解放军留下单位地址或电话,说应该通知他们所在的部队,如果发生意外好找他们。母亲觉得既然自己没什么大问题就不应该兴师动众的,人家在外当兵,也不容易,部队上知道了,这俩人还能不挨批评,弄不好还要受处分,人家的父母知道了在家也不得安生,母亲替他人想的比自己要多得多。母亲的小腿上有一块发紫的地方,痛了好几天才好,她也不敢作声,生怕大哥说她。
母亲上大学时,学的是英语专业,可是早已荒废了,退休后时间也多了,就想再学英语,我的二女儿送给她一本《英语九百句》,她每天读啊写啊,学的很起劲也还蛮有效果,四弟精通英语,曾多次出国访问,每次从北京回家母亲都要和四弟用英语聊天,让四弟纠正她的发音。有一次母亲到中国银行去取钱,满脑子的还是英语,“ Miss, please give me a withdrawal sheet.”(小姐,请给我一张取款单。)出口就是一句英语。柜台里的年青女孩一下了愣住了,连忙说:“对不起,您是要存款吗?”母亲笑了,改用中文说:“要说对不起的是我,你看我这老太婆怎么说起英语来了,我取款。”周围的人都露出诧异的眼光,这其貌不扬的老人竟然会说英语,母亲取完钱转过身自言自语地说:“活到老,学到老嘛。才能不得痴呆症。”大家都笑了。
改革开放以后,政策越来越宽松,一九八五年,在各地统战部门的帮助下,母亲由父亲陪同,和母亲的四哥、五哥、三妹、小妹等一行十多人在香港和台湾的大姐、大姐夫等亲人会面。离散四十年后的团聚,令人激动不已,台湾的大姐抚摸着母亲略显粗糙的手,禁不住泪水扑簌扑簌直流,“这么多年,你们是怎么过来的?”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受过的苦告诉分别多年的亲姐姐,只是平静地回答说:“我们过得很好,有退休工资,有医疗保险,什么都不愁。” 自此以后,台湾的大姐在经济上常常帮助母亲,母亲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,后来母亲大姐的丈夫病逝,大姐移居美国,至今与母亲保持密切的联系。一九九三年我们的父亲不幸因病去逝,虽有四个儿子,母亲却喜欢一人独居在武汉市汇通路的老屋里,母亲的大姐曾想接母亲去美国,母亲还是那句话“我过得很好。”谢绝了大姐的好意,母亲喜欢平静的生活。(待续)